范明静:佛教精神的独特的“心物观”
范明静:佛教精神的独特的“心物观”
苏轼佛教思想特征简论
范明静
[ 摘要 ] 在接受佛教思想的过程中,渗透儒道精神和苏轼个性的“真实”追求使他能超越偏执,获得不拘泥佛说的胜解,并用佛家的心性修养方法超越自身俗见,求得自我完善。苏轼对“真实”的追求在学佛的过程中始终与现实人生目标结合,实现了“静而达”的人生境界。熔铸佛教精神的独特的“心物观”是实现这种人生境界的关键。

[ 关键词 ] 真实 儒 道 佛 超越 静而达 心物观
探讨苏轼佛教思想的特征,他贬居黄州时所写《答毕仲举二首》可谓机枢。在此文中苏轼曾阐述自己对佛教及其思想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常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 ①可见,苏轼于佛说,所求乃“实美而真饱”,真实是他摄取佛家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弄清体现在苏轼身上的“真实”的内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佛教思想。
苏轼在《盐官大悲阁记》中,曾将学佛比做造酒。文中指出:“二人为之,美恶不齐。”原因在于“古之为方者,未尝遗数也。能者即数以得妙,不能者循数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与不能,而粗精见焉。”②这里的数即指造酒应遵循的“分齐”和“度数”,即一种客观规律,因此他反对“略其分齐,舍其度数,以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的态度,如果这样,“则其不为人之所呕弃者寡矣”。他还进而指出,“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也”,这意味着学佛是一种必须遵循一定客观规律的行为,“一以意造”必无善果。学佛还是要有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这和儒家提倡的“诚”不谋而合。《中庸》云: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③诚既指“天之道”,即自然的规律性,又指“人之道”,即一种至高的道德境界。圣人是思想行为合乎道理的人,用诚去实践诚,就是择取善并坚持它。诚者,真也。儒家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如盐化水,成为苏轼式“真实”的根底。理解这一点,便彻底划清了苏轼和佛教信徒的界限,方能洞晓他对佛教思想的受纳取舍为何。可以说,苏轼学佛,立足在儒。佛,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支持,而非安身立命的根本。
儒家的求“真”首先要求外在之理的“真”,如何去判定佛说的真实性呢 ? 在这一点上,苏轼有自己的标准。苏轼幼子为母王氏书《金光明经》四卷,送寺院收藏,以资其母之往生。并泣而问苏轼:“不知此经皆真实语耶,抑寓言也 ? ”苏轼借张方平的话作答:“佛乘无大小,言亦非虚实,顾我所见如何耳 ! ”又说:“我若有见,寓言即是实语;若无所见,实寓皆非。”④。在《与子由弟十首》之二中说“如人饮水,冷暖自如,死生可以相代,祸福可能相共,惟此一事,对面纷付不得”⑤,可见他并不以为佛乘是绝对真理,其真实性要以个人内在体验的真实性作为判断依据。这是苏轼对真实的追求所凸显的个性,反映出他坚持真实自我的一面。这种个性的由来,我们可以根据如下话语作出解释。苏轼之弟子由曾云“少 ( 指其兄东坡 ) 与辙皆 师先 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⑥ “得吾心”可以理解为个体精神上的共鸣。关于“真”,《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⑦此所谓“真”,既有“诚”的意思,即表里如一,内外如一,但更为强调的是表现内在性情的“悲、怒、亲”的真。苏轼引为同道,是很自然的事。注重真实自我,这是苏轼式“真实”犹为个性的—面。
儒家强调外在合理的“诚”和道家着重内在体验的“真”一体两面,熔铸于苏轼的人格和个性,构筑成苏轼佛教思想的受纳空间,并决定了他对这种思想资源的取舍。在现实人生中,求真往往意味着超越和坚执。在苏轼那里范明静:佛教精神的独特的“心物观”,学佛首先是对偏执的超越。儒佛道三家,各人皆有所取,但资质浅陋者多流于偏执。执其一端,排斥他方。苏轼并不是这样,他在《祭龙井辩才文》中写道: “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⑧他认为三家并无矛盾,其途虽异,其理则同,如江河滔滔,皆向大海。所以他在参悟佛理时,多注意多方融通。如在《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 >> 中云: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日:……以无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罗汉道,亦曰:……以无所得故而得。”如来与舍利弗若是同乎 ? 曰:何独舍利弗,至于百工贱技,承蜩意钩,履狶画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虽至于大菩萨苏轼的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其视如来,犹若天渊;然及其以无所得故而得,则承蜩意钩,履狶画墁,未有不与如来同者也。”⑼ 佛家成佛之道,在苏轼眼中被普泛化,显示出他超越一般信徒的眼界和理性。他还进一步以儒家的“思无邪”会通诸方。以为“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几于无所得故而得也。”各家本质类同的精神性活动,在苏轼那里定名于充满儒家色彩的“无所思心”,既显示了他儒家的立场,又涵盖了他家诸义。对偏执的超越,得到的是卓然不群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学佛而不拘泥于佛苏轼的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算是对佛家“无住”之意的真领悟吧。超越的另一面,是转身向内寻求自我完善,即儒家所倡导的“独善其身”。如何达到内在自我的完善呢?苏轼曾谈到学佛的体会:“任情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⑩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前面“无所思心”的具象化,儒家的目的,以佛家心性修养的方式获得,苏轼得到的,是他体验到的最高真实,不可言说。
苏轼于佛说中所求之道,是基于自我体验的真实,这种真实的最大特点,是始终与儒家一贯着眼的现实人生目标紧密结合,使他的人生不断升华到新的境界。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 他在《答毕仲举二首》中说道: “学佛老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⑾静而达,便是“实美而真饱”,也是苏轼对学佛的期许,这种追求,在苏轼遭遇人生巨大挫折被贬黄州后愈加明显。他在《黄州安国寺记 > 》中写道: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观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日: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 得城南精舍日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脩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⑿遭受打击后,苏轼自觉转到佛家的心性修养上来,求得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正是佛家所言的空静之境。从佛家禅宗看来,心是派生一切诸法,囊括宇宙,包罗万象的绝对神秘体。《坛经》中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能含万物色象,日月星宿,山河大地,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⒀不过,心倘若萦系于物,就称不得虚空了,此即所谓“心不住法即通流,住即被缚。”不住,即“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脩然,无所附丽。”故佛家之空静以破除对现实现象的执着为特征。苏轼虽能借助佛家静修之法消除现实人生的烦恼,但他亦对保持着对其消极一面的戒惧。这就是他曾提到的“静似懒,达似放。”佛家“空静”观消解了许多人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和对现实人生的关怀,从而流于惫懒和游戏人生。苏轼于静中所求并非如此,而是热烈地坚持着现实的情感和独立的人格,因为传统儒学执着于现实的理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一直是其封建士大夫文化人格的主干,成就一番功名事业是他一生难以割舍的人生理想。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指向使他于静所悟走向“达”的一面。其间的关节在于《超然台记》中独特的心物观。下面是对这种心物观的阐释: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哺糟啜醴,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无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 ? 物有以盖之矣 ! 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苏轼的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门,又焉知胜负之所在 ? 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 ”⒁ 如果我们从佛家思想与现实人生结合的角度观赏,对此段文字可作如下解读:佛家的空静观要求人做到“好恶美丑,无差别心”。苏轼推之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哺糟啜醴,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 ”基于静的功夫,首先于物无住,物无所蔽,心便获得解放,故能够“游于物之外”,游于物外便是超然,但并非不关心于物,因为苏轼看重的是“求福而辞祸”的“人之情”,他不能忘情于现实人生,故采取“观”的态度关怀于物。“观”是在去除与物的利害关系之后对物的重新发现,苏轼以这种发现为乐,因为凭借这种人生哲学,他便不是“进亦忧,退亦忧”,而是往往能处逆为顺,做到“进亦乐,退亦乐。
” 我们可以在他著名的《前赤壁赋》中,捕捉到这种从游于物内到游于物外,自忧转乐的心理轨迹:主客共临长江之水与山间之月,客“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对比于自然之永恒感叹其个体生命之短暂,折射出对生命永恒的执着,故黯然神伤。而主人却认为:“客亦知乎水与月乎 ?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 ”⒂跳出对个体生命的执着,将其置于宇宙之间,与万物共观,观出生命在别样意义上的永恒,于是“客喜而笑”。这是极为生动的例子。在诸多人生困境中,拜独特的受之于佛学而又不拘泥于佛学的心物观所赐,苏轼总能实现悲抑之后的昂扬,愁闷之后的澹定,这就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苏轼式的旷达。用之于做人,则可“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范明静:佛教精神的独特的“心物观”,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用之于观物,则能“尽物之妙”、“无往而不乐”,处顺而不自得,遇逆而不悲观,实现了超越常人的人生境界。
注释:
①《苏轼文集》卷 60 孔凡礼点校 中华书局 ②《苏轼文集》卷 12
③《四书章句集注》 36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④《书〈金光明经〉后》(〈〈苏轼文集〉〉卷 66 )
⑤《苏轼文集》卷 60 ⑥《栾城集》卷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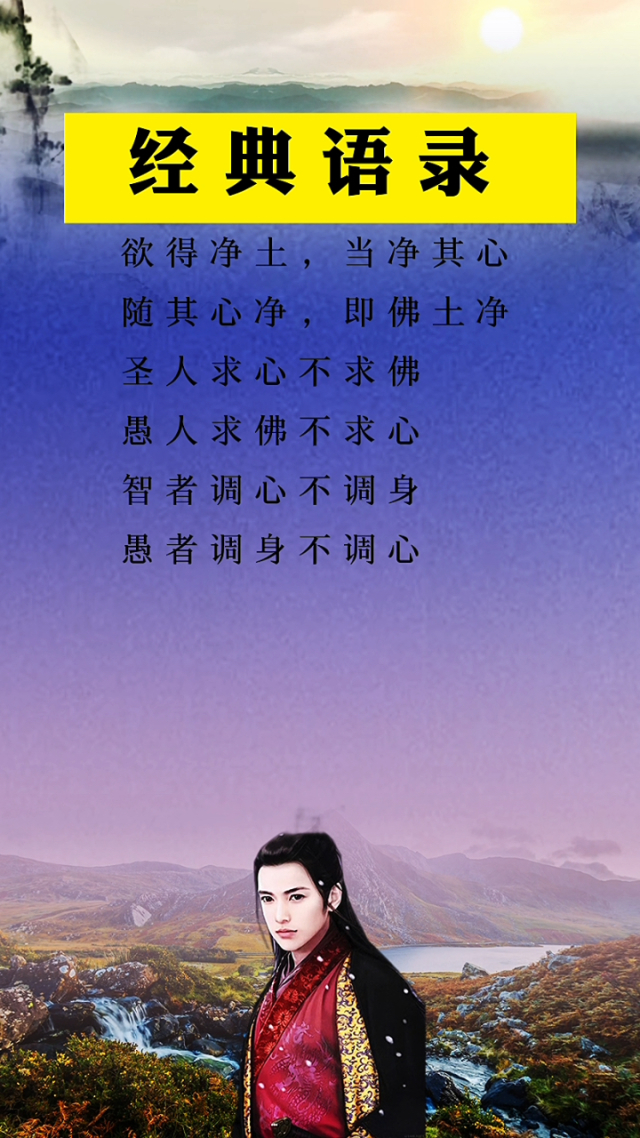
⑦《庄子今注今译》 823 页 陈鼓应 注译 中华书局 ⑧《苏轼文集》卷 63
⑨《苏轼文集》卷 60 ⑩《与子由弟十首》之三《苏轼文集》卷 60
⑾《苏轼文集》卷 60 ⑿《苏轼文集》卷 12
⒀《坛经第二 般若品》 ⒁《超然台记》(《苏轼文集》卷 11
⒂《苏轼文集》卷 1
随便看看
- 2024-08-12中国传统文化之民间艺术剪纸:瑰宝与奇葩
- 2024-08-12剪纸: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瑰宝,民间艺术的镂空之美
- 2024-08-10法学院党委:以党建促发展,推动学院各项工作稳步前行
- 2024-08-10第八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 21 世纪,依法治国和政治文明建设扎实推进
- 2024-08-10老子的大智慧及其现代意义:儒道互补与中华文化的发展
- 2024-08-09小六壬预测术:中华传统数术文化的瑰宝
- 2024-08-0760 甲子:天干地支的独特文化与计时方法
- 2024-08-05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问询函的详细内容
- 2024-08-05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及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 2024-08-04地方特色小吃:传承地域文化与代表当地人情风俗的美食瑰宝
- 2024-08-04书法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中国文化的道、礼、和
- 2024-08-04少林寺 4.52 亿郑州买地,进军房地产?真相来了
- 2024-08-03海派文化新论:梳理海派文化脉络,领略独特内涵
- 2024-08-03深入探究三教文化:儒、佛、道的融合与发展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
- 2024-08-0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及对企业经营的启示
- 2024-08-03深入领会红色文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 2024-08-02中华善本再生性保护网络传播活动:古代典籍的珍贵传承与保护
- 2024-08-0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 2024-07-31丁耘老师带领同学研读梁漱溟著作,探讨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
- 2024-07-31风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精髓与适中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