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谈儒学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思考建构未来世界的共同文明
黄玉顺谈儒学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思考建构未来世界的共同文明
来自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黄玉顺,以《人类共同文明的建构——关于儒学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思考》为题,在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作主题演讲。黄玉顺认为,“人类文明共同体”所指的“人类文明”,应当是面向未来的单数的“人类共同文明”建构。既不能是某种既有的单一文明传统成为人类共同文明,也不能仅仅是从既有的诸多文明传统中抽绎出不同文明间的共性,而只能是通过综合创造,建构一种新型的人类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人类共同文明”的创造,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寻求既有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交集就可以达成的,这种新文明不可能是运用归纳法的结果,而必须有某种创造性、革命性的思想观念突破。
“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文明”
应当是单数

“人类文明共同体”这里的“文明”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如果这里的“文明”是复数,那么,“人类文明共同体”就不新。因为人类世界历来就存在着不同的文明,而且其中一些不同的文明,向来就处在一个共同体之中。例如,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就不是由单一的文明传统构成的。事实上,欧洲或“西方”也不是由单一的文明传统构成的,而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全世界的不同文明如今都处在一个全球共同体之中。
由此可见,我们这里谈论的“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文明”,应当是单数,即是一个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概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将会迎来,或者应当建构一种怎样的“人类共同文明”?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当今世界“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立足当下,就是正视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面向未来,就是为消弭文明冲突而建构未来世界的共同文明。未来“人类共同文明”的建构,存在着以下几种可能:
既有的单一文明成为人类共同文明。古代帝国主义,这种天下主义,是由帝国的皇族掌控天下秩序。这种天下主义,实质上是宗法制度中的家族制度的国际性延伸,天下秩序的控制权掌握在皇族的手中。这就是古代意义的“帝国主义”。这种天下主义的政治理念,虽然自称“王道”黄玉顺谈儒学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思考建构未来世界的共同文明,但其所谓“王”,其实已非原来意义上的、列国时代的“王”,而是“帝”——帝国时代的皇帝。韩非子曾经非常准确地描述过这种天下主义的情形:“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所谓“圣人”,其实是指的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在西方,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的国际理念,都是典型的古代帝国主义。古代帝国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其“共同文明”其实是宗主国的文明传统,例如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儒家文明传统,欧洲的古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基督教文明的综合传统。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控制其他国家,并往往辅之以军事手段与文化手段,即所谓‘软实力’,由此形成一种世界秩序体系。
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发表了孔汉思等人起草的《全球伦理宣言》。但是,二十多年来,《宣言》所主张的“全球伦理”,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并未产生多大的作用。究其原因,刘述先归结为“理论上的不足”“实际上的无用”。“理论上的不足”即:这种经验归纳主义的“全球伦理”,缺乏真正的“全球伦理学”的支撑。正如真正的“全球伦理学”与“全球伦理”,真正的“人类共同文明”绝非既有的不同文明传统之间共性的简单归纳。
再者,上述经验归纳主义的一个前提,是对既有的不同文明传统的消极的维护。这些年来,这种维护的立场被表述为“和而不同”,意味我们应当承认各个文明传统的差异性、它们存在的合法性,同时应当和平共处、避免冲突。首先需指出的是,这其实是对“和而不同”表达的原意的曲解。
“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注疏》解释:“此章别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则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这就是说,孔子之所谓“和”,并不是说的各方乃至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和平共处,而是说的“君子心和”,即由于其不“争利”而心平气和的心态。严格来说,这与这里讨论的通过文明对话来创造一种新的文明这个问题没有关系。然而现实已经充分表明,被曲解的“和而不同”不仅并不能保证人类世界避免文明冲突,而且可能被利用来作为维护旧观念、旧价值和旧制度的口实儒家思想英语,成为各种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盾牌。
儒学在人类共同文明

建构中的作用
对于中国和儒家来说,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在人类共同文明的建构中,儒学应当、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传统儒学的许多文明价值,都可以贡献给未来的人类共同文明,而最核心的无疑是“仁”“义”“礼”等价值观念。
“仁”的文明价值是博爱。毫无疑问儒家思想英语,“仁”或“仁爱”乃是儒学的首要价值。正如程颢所说:“义、礼、智、信皆仁也”。这就是说,义、礼、智、信等价值,都不过是“仁”的展开,都可以由“仁”统合起来。
当然,“仁”或“仁爱”并非中国儒家独有的观念,其他许多文明传统也有相似或者相通的价值观念。例如,基督教也有其仁爱观念。不过,两者之间至少存在着三点区别:其一,基督教的仁爱或爱,根本上是上帝之爱;而儒家之仁爱,则是人自己的天然情感。其二,基督教的仁爱,是上帝之下的“博爱”;而儒家的仁爱黄玉顺谈儒学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思考建构未来世界的共同文明,则是人性先天平等观念基础上的“博爱”。其三,中西两种“博爱”之间还有一点区别,“博爱”原是儒家的一个概念,韩愈讲“博爱之谓仁”,孔子谓之“泛爱”,荀子谓之“兼爱”“兼而爱之”;而英语的“博爱”,本义是兄弟情谊。所以,人们用汉语的“博爱”去翻译英语的“”并不十分妥当。这个例子表明,在人类共同文明的建构中,“博爱”的价值至少应是中西“博爱”观念的某种综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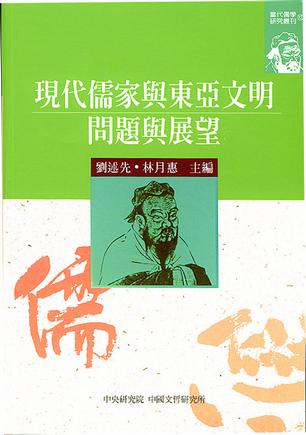
此外,还有一点区别尤其值得注意:儒家不仅讲“博爱”或曰“一体之仁”,还讲“差等之爱”或曰“爱有差等”。爱的差等性意味着:博爱的具体实现,是有亲疏远近的差异的——爱己胜过爱人,爱人胜过爱物。这当然是人类情感的实情。所以,儒家主张:“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义”的文明价值是正义。上面的分析,揭示出“仁”与“义”之间的一种决定关系。这表明儒家的“仁”“义”“礼”等价值之间并非平列并立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立体的理论结构:仁义礼。这其实就是儒家的社会正义理论——“中国正义论”。
在儒家的话语中,“义”指正义原则,包括: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及其制度的安排,贯彻一体之仁的精神;适宜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及其制度的安排,适应特定历史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儒学才能够穿透历史时空,不仅曾经建构了宗族王权社会的制度规范、家族皇权社会的制度规范,而且能够建构现代社会以及未来世界的制度规范。
这里需要注意,儒家所谓“义”,乃至通常所说的“正义”,具有两层不同的内涵:一层是“行为正义”,指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与制度;另一层则是“制度正义”,指社会规范与制度的建构符合正义原则,此是正义论的基本内容。后者是“正义”的更根本的内涵,因为人们之所以遵循某种制度规范,是因为这种制度规范本身是正义的,否则,人们没有遵守它的义务,倒有推翻而重建之的责任与权利。
“礼”的文明价值是制度。正义原则的确立,是为了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建构;反过来说,制度规范的建构,必须符合正义原则。这就是罗尔斯《正义论》开宗明义所指出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也就是“义”与“礼”之间的决定关系,孔子谓之“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义是礼的本质,礼是义的实行。
在儒家的话语中,“礼”并不仅仅指外在的礼仪,即不仅是“彬彬有礼”之类的形式。形式化的“礼仪”只是实质性的“礼制”的外在表现形式,而“礼制”又是原则性的“礼义”,礼之义即礼制背后的正义原则的体现。
这就是说儒家思想英语,礼是普遍的、永恒的。这是因为任何群体生活,都需要有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遵守这些制度规范。这也就是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但与此同时,礼又是特殊的、暂时的。这层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一套具体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具有普遍性、永恒性。这也就是孔子所讲的“礼有损益”。制度规范的损益变革,其价值根据即正义原则。
儒家的上述这一套“仁、义、礼”的原理,应当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体系。面对当今人类命运之“世界大变局”,这套原理应当发挥作用,为建构人类世界的新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和建构人类共同文明做出贡献。当然,其前提是在人类视野下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对话来共同创造。
总之,“人类文明共同体”所指的“人类文明”,应当是面向未来的单数的“人类共同文明”建构。作为这样一种文明,人类文明需要人类视野,共同文明需要共同创造,文明创造需要文明对话。在这种文明创造中,儒学可以贡献“仁”“义”“礼”等价值观。
随便看看
- 2024-08-09儒家角色伦理——21 世纪道德视野:挑战基础自由个人主义的当代伦理话语
- 2024-08-0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建构?
- 2024-08-08儒家伦理哲学 现代儒学编委会及主编徐波简介
- 2024-08-07孔子礼的思想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以仁为核心的多层范畴
- 2024-08-05大学:古代经典教材,现代道德启蒙,提升个人修养的必读之书
- 2024-08-03深入探究三教文化:儒、佛、道的融合与发展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
- 2024-07-30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传承深厚学术根基,铸就古典学术研究实体机构
- 2024-07-30敬畏天、遵循道:儒家思想的基础与本质,孔夫子的贡献及民族美德
- 2024-07-29国学经典弟子规为何被指伪国学?徐晋如痛呼其为毒草
- 2024-07-2920 世纪 50 年代后论语英译简史:多元化特征与多领域学者的贡献
- 2024-07-29安乐哲:醉心中国文化,推动中西哲学思想对话的美国学者
- 2024-07-28道家与儒家的思维差异:顺应自然与向内求的对比
- 2024-07-28梁氏国学功底深厚,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比较,探究先秦政治思想
- 2024-07-26第六届问道玉渊潭国际论坛: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探讨
- 2024-07-26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构社会价值和信仰体系——以曲阜为例
- 2024-07-26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
- 2024-07-26教育学萌芽阶段代表人物观点对比:孔子、孟子、荀子思想解析
- 2024-07-25传承国学传统文化:儒道释三家思想精髓与做人标准解析
- 2024-07-25儒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深远影响
- 2024-07-24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从孔子到董仲舒再到玄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