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尖锐指责:“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孔子尖锐指责:“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法家是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申不害,而由韩非集其大成的学派。儒学与法家在战国时期皆为显学,儒法二家在学术思想上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
春秋时期儒法之争 春秋时期早期儒法之争,反映于成文法的公布,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记载,晋国铸刑鼎,将晋国大夫范宣子所著刑书铸于鼎上公布。当时即遭到孔子反对。孔子尖锐指责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他认为公布成文法不如法在贵族手中而不公布更为有利,惧怕平民百姓根据成文法与贵族做斗争,不利于稳定上下秩序。孔子又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对此,晋杜预注说:“弃礼征书,故不尊贵。”(《春秋经传集解》第二十六《昭公二十九年注》)即认为人民据成文法做斗争,将不遵守礼的约束,而威胁到贵族特权。唐孔颖达疏:“民知罪之轻重在于鼎矣,贵者断狱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验于书,更复何以尊贵?威权在鼎,民不忌上,贵复何业之守?”(《春秋左传注疏》卷五十三《昭公》)这亦说明,公布成文法,民众可以据法与贵族斗争,使贵族不能随意所为。这表明,成文法的公布乃法制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应是进步措施。自春秋开始到战国时期,坚持成文法,成为法家学说的重要内容。
儒家与法家的对立,主要在于儒家尚德而不尚刑。儒家并非完全排斥刑,而是主张以德治教化为主,而以刑罚为辅,即省刑罚。孔子曾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是强调以礼乐教化为前提,而刑罚亦不能废止,但刑罚要依教化,离开教化则刑罚便会偏颇。孔子还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论语·颜渊》)“狱”指争讼,即狱讼,朱熹注“折狱”为“断狱”。上述引文说明孔子的弟子子路懂得司法。
战国时期儒法之争 战国时期法家大行,儒法皆为显学,一些重要法家人物与儒家有师承关系。如战国初期以改革著称的魏文侯即曾以孔子弟子子夏为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魏文侯任用为相的前期法家李悝(李克),亦受业于子夏。《汉书·艺文志》著录《李克》7篇,列为儒家。《晋书·刑法志》说李悝著有《法经》。战国末期重要法家韩非、李斯均为儒家荀子弟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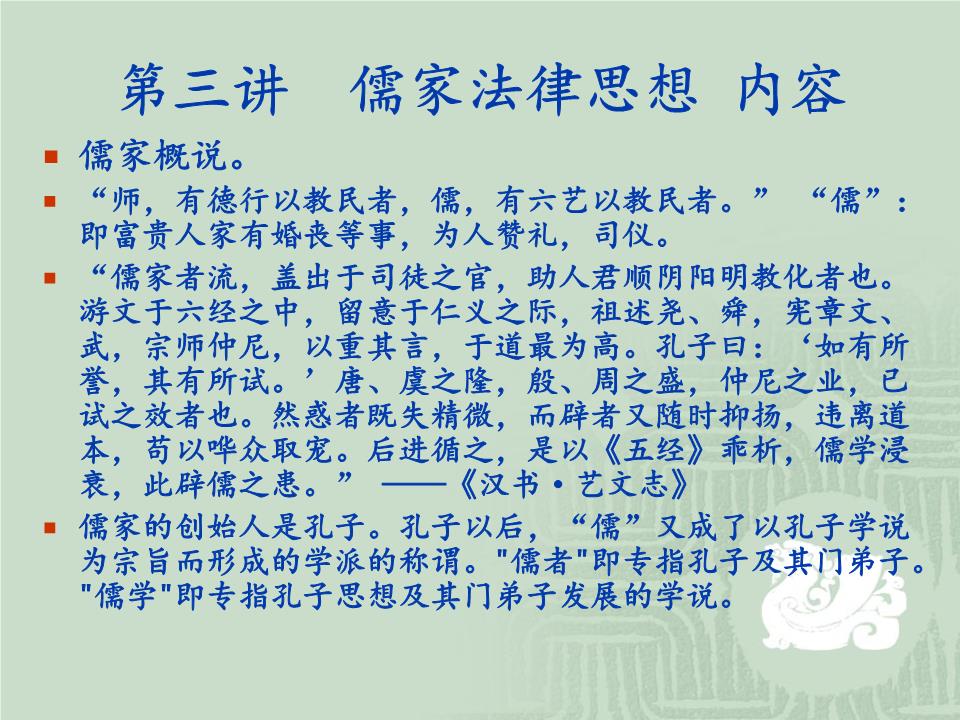
法家虽与儒家有师承渊源,然因学术宗旨不同,互相抨击亦甚剧烈。如秦国经历商鞅变法而富强,法家耕战主张为群雄所接受,但遭到孟子尖锐抨击。孟子说:“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下》)孟子所攻击的“良臣”儒家思想法家思想,乃法家耕战之士孔子尖锐指责:“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他斥他们为“民贼”,是因为法家重功利而不重仁义。孟子目睹当时诸侯提倡耕战而使兼并战争规模愈来愈大,为人民带来了战乱之灾。因此,他强烈反对法家耕战主张,而主张实行王道反对霸道,以仁义争取天下归顺。战国末年,荀子亦批评法家慎到、田骈、邓析等人思想“不可以经国定分”和“不可以为治纲要”(《荀子·非十二子》)。苟子也是强调实行仁义,即“经国定分”,要用礼义,而非用法治。所谓“为治纲要”即尚德治教化,而非尚刑罚。荀子曾和弟子李斯辩论仁义和权谋问题,李斯认为秦国富强“非以仁义为之,以便从事而已”(《荀子·仪兵》)。荀子反驳说他是“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本即指仁义,而末指权谋。
儒家仁义主张也遭到法家尖锐抨击,如韩非作《五蠧》批评“儒以文乱法”,还说儒者“称先王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韩非认为战国争雄要靠实力,只有实行耕战才能富国强兵,他说:“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攻战,则国何利焉。”(《韩非子·八说》)因此,韩非认为儒法不两立,他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显学》)秦始皇实行法家主张,摈斥儒家仁义,虽取得天下统一,但因为政惨刻,不久便激起人民揭竿反抗,秦统一仅15年便灭亡了。
汉代之阳儒阴法 汉代封建中央集权大一统形势的出现,儒法之争的格局又发生新的变化。汉代朝廷吸取秦亡教训,改变秦朝严酷少恩的重法主张,实行“霸王道杂之”主张。汉武帝定儒家为一尊,这时的儒家实际上吸收了法家思想。近人章炳麟说:“然则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已。今夫法家亦得一于《周官》,而董仲舒之《决事比》,引儒附法,则吾不知也。”(《訄书·儒法》)章炳麟认为儒法二家思想是互补的,因此,儒家并非摈斥法家,法家思想来源之一为儒家《周官》(指《周礼》)。而儒家董仲舒作《公羊决狱》(《汉书·艺文志》有著录,已佚。后人马国翰等有辑本),亦吸收法家主张,即引儒附法。由此可以看到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术之中则吸收有法术。史称汉代阳儒阴法,即指汉代儒学以仁义德治为外衣而装有刑名法术的内容。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宣帝纪》)此所说。汉家自有制度”儒家思想法家思想,当包括汉武帝独尊儒术在内,说明武帝定儒家为一尊,实质是“霸王道杂之”。《史记·汲郑列传》载汲黯曾指责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亦说明汉武帝并非纯任儒术。汉唐以后历代王朝基本上沿袭“霸王道杂之”主张,此亦为后儒颂扬三代而讥讽汉唐的原因之一。
宋儒之儒法观念 宋代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成熟,封建纲常更为强化,儒家独尊地位亦更为加强。理学家发扬儒家崇王黜霸、重礼轻法主张,更加强调王霸义利之辨。理学家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在理论上更加摈斥法家功利主张,甚至视法家为异端。宋儒程颐说:“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氏之害,甚于杨、墨。”(《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道篇》)这是将申(不害)、韩(非),杨(朱)、墨(翟),佛教统统视为异端,尽管其为害程度有别,然而均属有害无益学说。程颐还以申、韩与老子有思想渊源攻击老子说:“老子语道法而杂权诈,本末舛矣。申、韩、张、苏皆其流之弊也。申、韩原道德之意而为刑名,后世犹或师之。苏、张得权诈之说而为纵横,其失亦远矣,今以无传焉。”(同上)这里从思想渊源上批评了老子和申、韩、苏(秦)、张(仪),而认为申、韩之刑名较之苏、张之纵横,尚有可取之处。程颐在理论上批评法家,而在实践上则并不排斥刑罚。他说:“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刑罚立则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虽日尚德而不尚刑,顾岂偏废哉?”(《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政篇》)德和刑二者不可偏废,虽以德治教化为主,但离开刑罚则亦难求治,刑罚起辅助教化的作用。
宋儒朱熹亦主张“为政以德”,然亦认为刑罚为德政所不可缺少,他说:“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论语集注》卷一《为政篇注》)这里将德礼和政刑二者之本末关系说得极为明白.德礼为本,政刑为末,不可弃本逐末。然而末亦不能废,朱熹又说:“圣人为天下,何曾废政刑来!”(《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论语五·为政篇上》)这亦是强调德治并非排斥刑罚,只是德和刑本末不能颠倒。朱熹生当南宋偏安时期,他曾从政为官,这也使他在仁义和法治关系上产生务实精神。他虽然在理论上崇仁义而抑法治,而在实践上则亦体会到法治之不可缺少。他说:“古人为政,一本于宽,今必须反之以严。盖必如是矫之,而后有以得其当。今人为宽,至于事无统纪,缓急予夺之权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八《朱子五·论治道》)朱熹这里一反儒家以宽为本的政治原则,主张反之以严儒家思想法家思想,是有所为而发,并非否认儒家崇德抑刑的根本主张,而是针对当时社会实际状况以重法抑奸豪。申平民,其实质仍与儒家为政以德的宗旨相符合。
近世之评价 近代儒家王先谦作《韩非子集解序》云:“(韩)非论说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严刑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孔子尖锐指责:“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幼孤得长。此则重典之用,而张弛之宜,与孟子所称及闲暇明政刑,用意岂异也?”这里予韩非的法治思想以极为肯定的评价,而且和孟子思想相提并论,与宋儒崇孟黜韩宗旨大相径庭。这反映近代社会历史的变迁,对儒家仁义的框框有所突破,而对韩非等法家亦有了新的评价。
随便看看
- 2024-08-09儒家角色伦理——21 世纪道德视野:挑战基础自由个人主义的当代伦理话语
- 2024-08-0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建构?
- 2024-08-08儒家伦理哲学 现代儒学编委会及主编徐波简介
- 2024-08-07孔子礼的思想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以仁为核心的多层范畴
- 2024-08-05大学:古代经典教材,现代道德启蒙,提升个人修养的必读之书
- 2024-07-30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传承深厚学术根基,铸就古典学术研究实体机构
- 2024-07-30敬畏天、遵循道:儒家思想的基础与本质,孔夫子的贡献及民族美德
- 2024-07-29国学经典弟子规为何被指伪国学?徐晋如痛呼其为毒草
- 2024-07-2920 世纪 50 年代后论语英译简史:多元化特征与多领域学者的贡献
- 2024-07-29安乐哲:醉心中国文化,推动中西哲学思想对话的美国学者
- 2024-07-28道家与儒家的思维差异:顺应自然与向内求的对比
- 2024-07-28梁氏国学功底深厚,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比较,探究先秦政治思想
- 2024-07-26第六届问道玉渊潭国际论坛: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探讨
- 2024-07-26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构社会价值和信仰体系——以曲阜为例
- 2024-07-26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
- 2024-07-26教育学萌芽阶段代表人物观点对比:孔子、孟子、荀子思想解析
- 2024-07-25传承国学传统文化:儒道释三家思想精髓与做人标准解析
- 2024-07-25儒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深远影响
- 2024-07-24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从孔子到董仲舒再到玄学
- 2024-07-24儒家思想:孔子创立的完整思想体系及其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