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先进和关心佛教的近代佛门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百年近代史是中华民族艰难选择、曲折前行的悲壮历程。在民族危亡关头,在民主与科学的狂飙大潮下,传统文化受到严酷挑战,各种新学说揭竿而起,佛教此时必须为自己的存在辨护,寻找自己的历史位置。
中国佛教至清末已是衰落不堪,不仅僧团窳败、义学凋敝,而且蛊惑迷信,逃禅避世,愈来愈背离社会主流和中心。这种状况遭致了有识阶层的鄙视与抨击,酿成了全国范围的“庙产兴学”风潮,本已岌岌可危的中华佛教更是风雨飘摇。基督教咄咄逼人的扩张,更有新文化运动“以科学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使佛教的生存状况异常严峻,佛教革新图存的问题由此尖锐地凸显出来。不少佛门先进和关心佛教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振兴佛教、适应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紧迫性。不仅要在教制、教产等方面进行改革,更重要的是要针对时代潮流和社会现状,对佛法观念进行自觉调适,以求契理契机地重构佛教新形象,谋求佛教的新发展。
何建明博士新著《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以翔实的历史资料,细致的条分缕析,对中国佛教为适应时代而进行的自我反思、内向发掘、扬真避伪、转换重构,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论述,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佛教的重大革新和佛门先进的种种努力提供了极大方便,对反思和展望中国佛教的建设,其意义不可小视。
关于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该书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而我认为其核心是佛法入世与出世关系的调适。在以往佛教观念中,已有不少调和入世与出世关系的论述,虽然这些主张并未在实践中真正占据主流,并未根本改变佛法以出世为主导地位的传统思想,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大乘佛法具备了融通世出世法关系的内在条件,也就是说这一问题在佛法的理论内涵中可以找到解决的根据,而且也反映佛法适应时代、面向现实的变化是一贯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只是到了近代,现实化的方式和程度更深刻、更剧烈。
近代佛教由出世趋向世间的重大转换,作者进行了四个梯次的归纳。针对当时将佛教尽归为消极厌世的排佛观点,佛门先进和有识之士首先指出“佛法非厌世,非消极”。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早在戊戌变法前后,便汲取佛教的一些思想佛家的出世思想,阐发其资产阶级改良主张,尤其是谭嗣同所表现出的佛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无不说明佛法中蕴藏着能够适应时代的积极因素。梁启超也强调佛教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其“学道而至于庄严地狱,则其悲愿之宏大、其威力之广远,岂复可思议也!”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更是明确提出复兴佛教。他认为佛教之“依自不依他”的精神,无我之大无畏气节,非常值得汲取发扬。他针对时人的排佛议论指出,佛教所厌之世“乃厌此器世间(物欲),而非厌此有情世间(生物与人类),以有情世间堕入器世间中,故欲济度以出三界之外。”肯定了佛法并非一味消极厌世。由于他们的倡言力行,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些进步报刊上涌现了不少以佛法鼓动民众的文章。
进入民国以后,圆瑛法师、弘一法师和以欧阳渐、王恩洋、吕澂为中坚的金陵学派,也大力倡导大乘佛法积极救世之精神,认为“佛法非消极、非退屈,治世御侮、济乱持危,均为菩萨之所有事”,反驳了以佛法为消极厌世的指责。太虚强调,佛教中虽有出世避世的一面,多属环境使然,并非佛法之本质。佛法真义,不仅不是厌世主义,而且是积极的救世主义。
在回击排佛之士的片面责难之后,佛法真实形象得到了维护,确立了佛法存在的合理性,也为佛法由专重出世为趋向现实扫清了初步障碍,奠定了认识基础。接下来问题势必深入到从更深层面上讨论佛法与世法之关系,或者说,从本质层面辩明佛法与世法之融通。所以佛家的出世思想,作者以讨论“佛法与世法,本来不二法”作为佛法观念转向现实社会的第二梯次。
20世纪初,宋恕便提出了出家只是学佛之始,并非学佛之终的观点。他以人道阐释佛法,有意学习日本真宗和欧洲基督教之改革经验,推动佛法由“主出世”而走向适应现世,从而开一时风气之先。20年代太虚提出了“行为主义之佛乘”,批评当时佛教徒大多囿于成见,只知佛法为出世法,而不知佛法即是利益人群的世法。他强调“人间世无一非佛法,无一非佛事”。圆瑛也积极著文融通佛法与世法,认为“佛法不离世法,欲以真谛而作世谛流布。”金山寺宗仰法师也提出“以佛法作世间法而说”,提高国民道德,增进灵思智慧,认为“世法与佛法平等将通邮”。

在他们的影响下,佛化新青年会提出了“生活的佛学”,强调佛法本来不离世间,做好平常事就是佛道。佛法必须解决人道、人群问题佛门先进和关心佛教的近代佛门,“决非迂阔寥远,隔断世法”。杨度的“新佛教论”也反复强调“入世即是出世……所以不说过去、未来,只说现在;不说出世,只说入世;不说神道,只说人事。”在二三十年代,不仅有许多学佛居士积极推动佛法观念的现世化,而且一些开明的寺僧,也开始自觉地融会出世法与现世法。灵隐寺慧明法师从“法法圆融,兼合互摄”的角度,指出入世出世不相隔离,“入世出世尚且是假名……佛法真理不离世法,出世入世完全在于自心。心正,入世也是出世;心不正,出世也是入世……世法和佛法,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他用“佛法与世法,本来不二法”概括佛法与世法道理一贯。著名高僧印光大师晚年也从心性着眼,融通世法与佛法。
据此,作者指出,至四五十年代,近代佛法观念的现世化,已成为佛学的主流,并逐步走向了理论的总结阶段。印顺和吕澂二人则为代表人物。
印顺剖析了传统佛学中偏重出世的思想根源,他指出:“古德虽极力说明性空不碍缘有,但实际是对于有发挥得太少了!大都依有明空,忽略反转身来,从空去建立正确合理的有——一切实际的思想行为。今后应该在这方面特别注重发挥。”否则,就会“使佛法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汩没佛法的觉世大用。”他指出,佛法与世法本来不二法,以往佛法偏于出世,将两者视为二,现在世人把佛法完全等同于世法,将两者视为一,均偏离了佛法之圆融完满。吕澂认为出世并非舍弃厌离我们生活着的世界,而是觉悟了本性的真相,超脱生死的流转轮回,乃“出类拔萃之为出”。他强调:“佛法用于行世,不离世间,所着重不在世间即涅槃之上,……乃着重于实践世间之实际而为涅槃,涅槃应统实践过程而言。”必须先拣除了小乘的说法,才能真正弘扬大乘佛法的现世积极精神,从而真正契理契机地适应现代社会之需要。作者在评价了二者的论说各有所长后,肯定了印顺和吕澂对佛法与世法关系问题的深化和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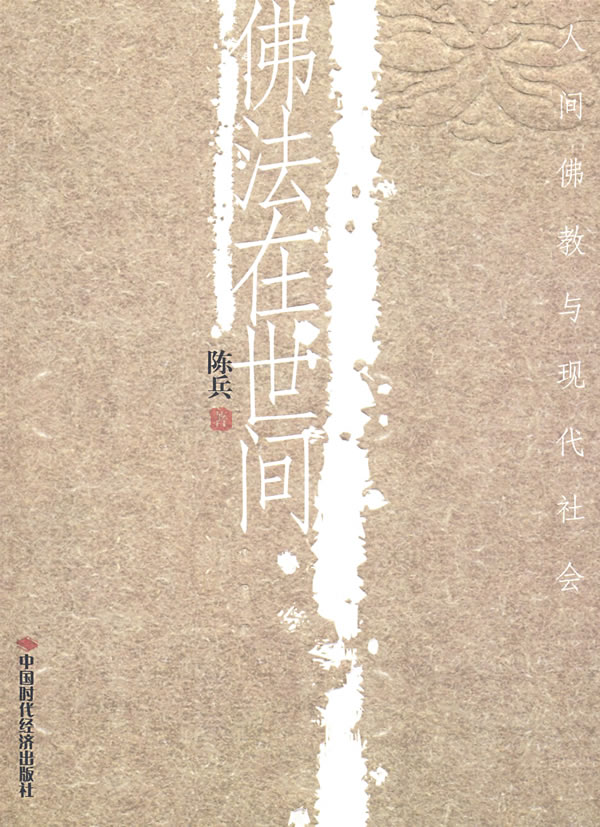
在理论层面融通了佛法与世法后,佛法观念通过近代调适,应该说在观念上已基本完成了现实化转向,近代佛教所要做的便是如何现实化,或者说如何使佛法在现实社会中具体地发挥积极作用。所以接下来,作者将问题深入到第三层,“真正人生,则佛法人生”,讨论佛法以人生问题为契机对近代社会所做的应对与影响。
作者认为,人生问题,是佛法面向现实的根本问题。在简要叙述了人生问题上近代佛教曾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有过影响后,作者把近代佛法人生观的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伦理原则。印光、虚云、谛闲、圆瑛等都援儒入佛,来强调和阐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二是“为众生服务”的人生观。圆瑛法师在前者基础上,根据大乘佛法的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精神,提出仅仅做个本分好人尚不够,更应担当起积极救世、普度众生的责任。宁达蕴、李石岑、周叔迦等人也积极倡行佛法的“无我”、“利他”人生观。30年代释东初还提出了以大乘佛法精神来“彻底改革当今的国民性周易学院,破除那宗法社会传统自私自利的人生观理想”。福善在当时影响极大的佛教刊物《海潮音》上撰文呼吁,以菩萨为众生服务的人生观反对法西斯主义,为解救众生,菩萨也会抡刀上阵。反映了当时人生观问题与民族救亡相结合的历史自觉,佛教人生观进一步发展成为“为众生服务”的救国救民的人生观。三是“达观、无畏”的人生观。颇具代表的是梁启超、常惺、王恩洋等提出了艺术化人生,高扬人生的伟大,追求以“圆满正觉的菩萨心”和“悲智双运的菩萨行”,来实现“人己共进于永久快乐的”人生境界。抗战时期,广大爱国爱教僧俗则大力弘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与革命乐观主义人生观联系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妙谈还强调要真正做到“大雄无畏”,就要培植起伟大雄厚的力量,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探求“五明”,学习知识和技术。“知识就是力量”,从佛法角度在一位40年代的中国寺僧这里得到了阐扬,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佛法自我调适的内在潜力。四是“平等、自由”的人生观。平等、自由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专制主义中提出的社会原则和理想,在近代中国也引发了广泛的回响。而当时不少先进人物,如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杨度等均从佛法教理中寻找平等、自由的思想资源。太虚法师提出了大乘佛法人生观,并从佛法角度论证了自由、平等人生观是佛法本质内容。他甚至说:“全世界的人们都能依着无我唯心的宇宙自然的法则去活动,平等自由的人生目的就会实现了。”当时佛门先进也均肯定佛法主张的平等自由较之西方人本主义更深刻、更广泛。佛法对人生观的以上影响显示了佛法与世法的融通佛门先进和关心佛教的近代佛门,具体表现了佛法趋向现世的自我调适,进而与时代的契合。
最后作者将近代佛教现世化运动引向其归宿,即第四梯次“从‘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作者指出;“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是中华佛教面向近代社会人生问题所进行的一次契理契机的伟大革新。阐扬佛教的现实人生理论,是中国佛法观念近代转变的重要特征。”作者高度评价了40年代后印顺法师在推动太虚提出的“人生佛教”,并将其深化阐发为系统的“人间佛教”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取得的卓越成就。印顺的“人间佛教”力图摆脱佛教末流注重来世、侧重出世的观念,强调“真正的佛教是人间的,惟有人间的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义”。在台湾,人间佛教的实践已成为当今世界引人瞩目的宗教文化潮流之一。在大陆,以赵朴初居士为代表的佛教界也明确提倡“人间佛教”,力图“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这表明近代佛教趋向现世已从观念的转变调适,走向了广阔的社会实践。
佛法由出世趋向现世是近代佛法观念转换调适的核心。正是由于近代佛教走向现实社会,才开展与科学的对话,提出“佛法非违背于科学”佛家的出世思想,“佛学可以补科学之偏”,以应对把佛法当成迷信加以批评的科学化运动,使佛法能在科学时代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才开展了同近代社会政治观念的对话,使佛法在逐步开放的社会中,与平等、民主、和平与自由的理性法则相呼应;进而也才能够使佛法与其他宗教、哲学等文化形式开展广泛的对话,在发挥佛法特质并在与现代文明结合中,努力“造成世界人类的中正和平圆满之文化”。所以,佛教现世化是整个佛法观念近代调适的核心,其它方面的调适可以说均是这一核心的逻辑延伸,是佛法面向现实社会的具体展现。
但是佛法不可能要求完全地入世,否则便成为世法世学中的一种,而非具有终极关怀和信仰价值的宗教。该书作者也注意到,佛教的现世化,即使是“人间佛教”,也没有放弃它的出世特性。出世即“觉悟”后的对现实社会的根本超越性,只不过近代佛教强调这种“觉悟”不是在避世中实现的,而应是在人世中实现的,是即世而超越,非离世而超越,从而使超世与救世有机结合起来。正因如此,近代佛教极大丰富了佛法的内涵和践行空间。佛法是世法与出世法的统摄圆融,佛教的现世化并不能归论为纯粹的世俗化。在近代文化演义中,以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由佛归儒,正是由强调佛法的入世法,而放弃了佛法的出世法,所以走向了以儒代佛,而不是对佛法的更新发展。而以圆瑛、欧阳竟无、王恩洋、印顺等为代表的另一批人,则摄儒入佛,重世间法,但坚持了出世法,从而在将中国佛教从出世主义的泥潭中拯救出来的同时,契理契机地捍卫了佛教的立场。在佛法中入世与出世的关系实际也就是机与理、俗与真、用与体的关系,弘扬一方遮蔽另一方,均破坏了佛法的圆融性,甚至可能蜕变为非佛法的东西。可惜该书作者在这方面的论述略显不够。
总之,作者以洋洋三十余万字的篇幅,全方位论述了中国佛教在对古代佛教优秀传统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立足中国近代的历史环境,并在东西方宗教文化和非宗教文化的重要影响和刺激下,进行的全面而深刻的自我调适和更新,从而使近现代中国佛教走向了传统性与现代化、民族性与世界化的合理发展之路。而作者对中国近代佛法调适的核心——“由出世而趋向世间”所作的层层深入、剖析分明的叙述,是读者体会最深、受益最大之处。于是反刍如上,愿更多读者关注品鉴。
随便看看
- 2024-08-12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的传奇人生
- 2024-08-11探究僧官系统的世俗化:从机构建制到任官模式的演变
- 2024-08-09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及制度的影响:冲突与融合
- 2024-08-08探究中国佛教在越南的传播历史及中华文明的影响
- 2024-08-04北京大学:优秀学子的梦想之地,哲学系的独特魅力
- 2024-08-03深入探究三教文化:儒、佛、道的融合与发展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
- 2024-08-02王颂: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其佛学辞典研究成果一览
- 2024-07-31丁耘老师带领同学研读梁漱溟著作,探讨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
- 2024-07-22佛教思想的核心戒定慧,其起源与释迦牟尼的生平及影响
- 2024-07-22佛教思想主张众生平等,业报轮回劝人弃恶从善
- 2024-07-21佛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及教义角度的归纳
- 2024-07-20敦煌莫高窟画中有话系列赏析:领略千年佛教艺术的魅力
- 2024-07-20红木家具与工艺品:北宋大才子苏东坡的佛教渊源
- 2024-07-18佛教文化中的因果定律:善良是否有回报?
- 2024-07-17七步莲花:佛陀的诞生与佛教的起源,探寻古印度的宗教奥秘
- 2024-07-17因果报应真的存在吗?心理学研究揭示行善能延长寿命
- 2024-07-17慈悲为怀与因果报应:探索佛家思想中的人生哲学
- 2024-07-15儒教、佛教、道教:三教传统宗教的特点与影响
- 2024-07-12人生迷茫时,佛教智慧能否带来解脱与快乐?
- 2024-07-05佛教养生理念与方法:修心养性,从心开始,追求健康长寿
